邯郸未成年人罪案:重刑能对抗恶意吗?
文 | 李厚辰
最近,邯郸未成年人故意伤害案引起了很大的讨论。很多人呼吁重刑,认为重刑不仅是对犯罪者的惩罚,还是防范未来犯罪的必要警示。
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应勇也于近日表态:“对未成年人实施的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犯罪,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,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”
这番表态是对汹涌民意的回应,网络上主张重刑的人取得了阶段性成果。发生如此骇人听闻的案件后,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是好事,但最高检的回应,几乎已经定调嫌疑人会被追究刑事责任。
另一面的理由算是老生常谈,即青少年犯罪和霸凌并非一个个体责任问题,而是一个社会问题。这种问题必须通过留守儿童、学校管理等一系列手段来解决,而非严刑峻法。
每每这种问题出现,就似乎是“严刑峻法派”与“社会结构派”之间分歧的一再重演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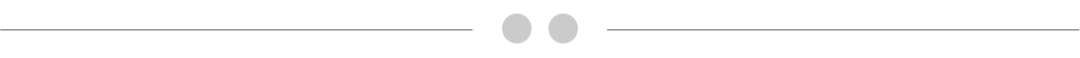
《小武》
其实这种事件是对社会和个体进行系统性反思的机会。芬兰赫尔辛基在2020年曾发生了3名青少年虐杀的残忍案件,涉事少年分别被判处8-10年监禁。
更重要的是,事后引发了芬兰对未成年人教育和社会体系的全面反省,也有专著出版深入探讨了这起案件背后的社会和个人层面的问题。除了关注处罚力度,这类探索或许能产生更长远的意义。
这个问题没有任何短期的解决方法,“社会整体参与”展现了理论上的可能性,而严刑重罚也并不能一次性解决问题。我们再次遇到要与问题长期共存的处境。但是,长期共存绝不等于消极等待,起码有几个方向是可以改善和关注的:
1)社会福利体系完善
呼吁资源向福利体系倾斜,通过不断完善福利体系,让社会问题得到缓解。这也不是抽象的,现在国家鼓励“新型城镇建设”,并以“县域经济”为主要抓手。如果可以促使农村人口通过这个机制转城市户籍,享受哪怕入门级的城市福利体系,可能都会是有益的发展。
2)社区建设
现在的社区建设主要以行政管理为主,但“中央社会部”建立后,资源也有向社工领域倾斜的可能。如果以社会末端的秩序作为考核,给予基层社会自治的空间,或许能提供更多社工与社会职能。
3)出生率降低下的教师资源密集化
出生率下降后大量幼儿园和小学教师资源冗余。如果增加教育投入,我们也会有现成的人手和足够的经验优化学校的管理,甚至对留守儿童、边缘青少年进行辅导,提供校舍进行住校管理等。
谁都希望过平稳的日子,如果生活尚有希望,大概鲜有人是“天生犯罪者”。也许下次,我们不必只呼吁“重罚”,而是尝试呼吁类似的上述建议。问题不会在短期内得到解决,但我们可以尝试向一个能解决复杂问题的社会,迈进一步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