被忽视的成人多动症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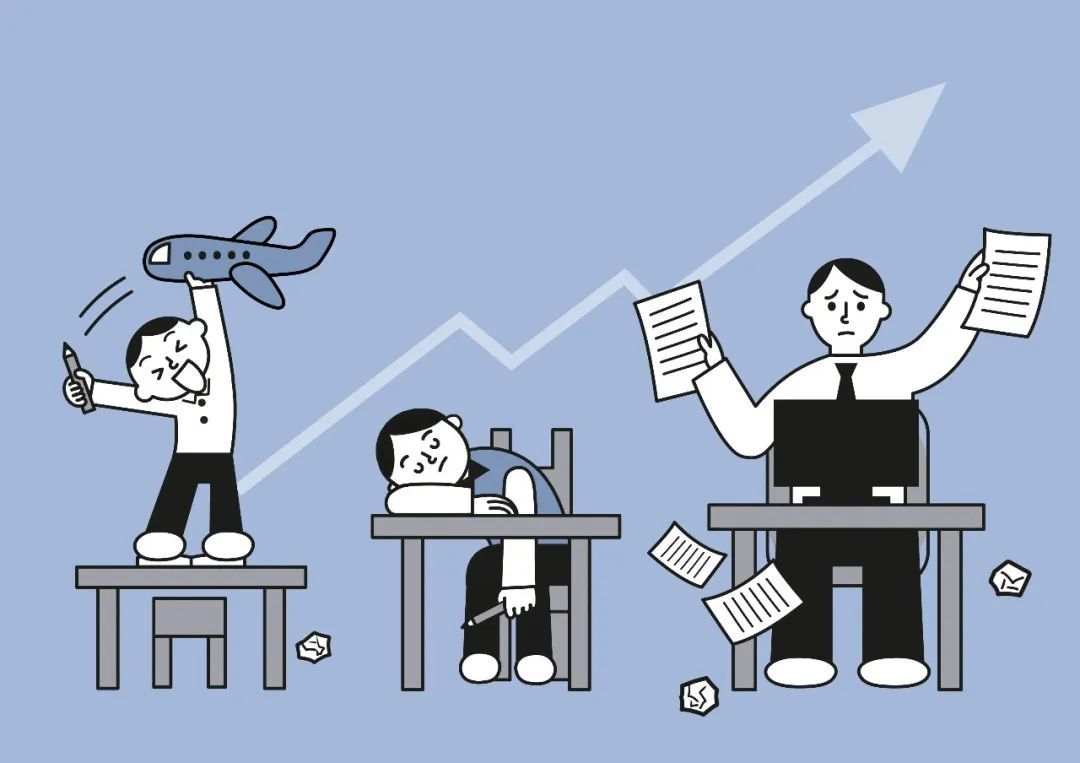
覃艳华
成为ADHD之后
白瑶从小就知道,自己在他人的眼中是个“坏小孩”,时间一长,她也不断地陷入自我怀疑。
确诊后,她没有松一口气,反而多了几分羞耻,和觉得前路更困难的悲楚。
有时,白瑶忘记赴约,跟朋友解释,这不是故意的,是真的生病了,名字叫ADHD。对方一个眼神,她就知道,又被认为在找借口了。
白瑶没有放弃自救。她会随身携带一个备忘录,事事都记录,但仍会有些遗漏。她买了一个儿童专用计时器,什么时间该刷牙、看书、学习,都要依靠计时器。
如今成人ADHD的讨论度变高了,分享的人变多了。如果公开承认,白瑶担心会被人认为“赶时髦”,但她也很难受,自己明明被医院确诊,凭什么不能提?
谢阳记得曾和前任说过自己可能有ADHD,但对方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:“你只是疑神疑鬼。”
有时连家人都无法接受孩子患病。子女努力描述症状,父母却在淡化,将一切都归于“哪个小孩子不这样?”“孩子小时候拖拉、懒散、淘气、丢东西不是正常的吗?”
无法互相理解的亲子会在诊室爆发矛盾。覃艳华遇到这种情况时也很无奈,不能达成一致就无法就诊,更无法治疗。
更多时候,覃艳华会在旁边解释,“本来你们孩子智商很好的,打个比方,按他的智商可以考清华,但是因为注意力不集中,他只能考个二本的学校。”家属一听就明白了,大多都会选择配合治疗。
国内对于成人ADHD的关注度逐渐提高,但社会性支持仍不够。根据《美国残疾人法》和1973年康复法案,ADHD被认为是一种残疾,患者等同于残疾人,其权利受法律保护。
美国健康杂志《ADDitude》是一份专注于注意力缺陷障碍的杂志,它指出,雇主应该为ADHD患者提供安静的工作环境;允许降噪耳机或白噪音;有时或所有时间在家工作等。
患有多动症的学生受到美国州和国家法律的保护,保证他们接受免费和适当的公共教育。
雅思考试的官方网站也对ADHD患者提供相关政策:拥有25%额外的听力时间,即可以重复两遍听力文本;额外25%的阅读和写作时间;有监督的休息时间;单独的监考等。
知乎那个提问,有一位答主答道:“ADHD”的生活状态最像鲨鱼,那种一刻也停不下来的“胡思乱想”,就像鲨鱼在海里需要一刻不停地游,一旦停下来就会沉入海底。而朋友、家人,任何一个可以理解或接纳自己的人,都会成为打怪时杀敌的利器。
白瑶在讲述中,反复提及了好朋友给她的力量,在她马上沉入海底时,托住她。在她需要每天被酒精催眠的日子里,朋友经常陪她吃饭。一年后,白瑶戒酒了。
读高中时,白瑶还是休学了。半年后,她转学到了另一个城市,遇到了新的老师。高四那年,她需要重新回到家乡高考,历史老师把她送到了学校门口。在路上,历史老师说,你是我教过最好的孩子,你一定能考上你想去的学校。
“那句话温暖了我好多年。”白瑶也做到了,考入了理想的学校和专业,从事了从小就追求的工作。
现在的她更愿意站出来,分享身为“ADHDer”的经历,让更多的人,可以在黑暗中点亮前方的树根。
(文中白瑶、谢阳均为化名。)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