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京按摩女日记:我去华人的“大保健店”面试了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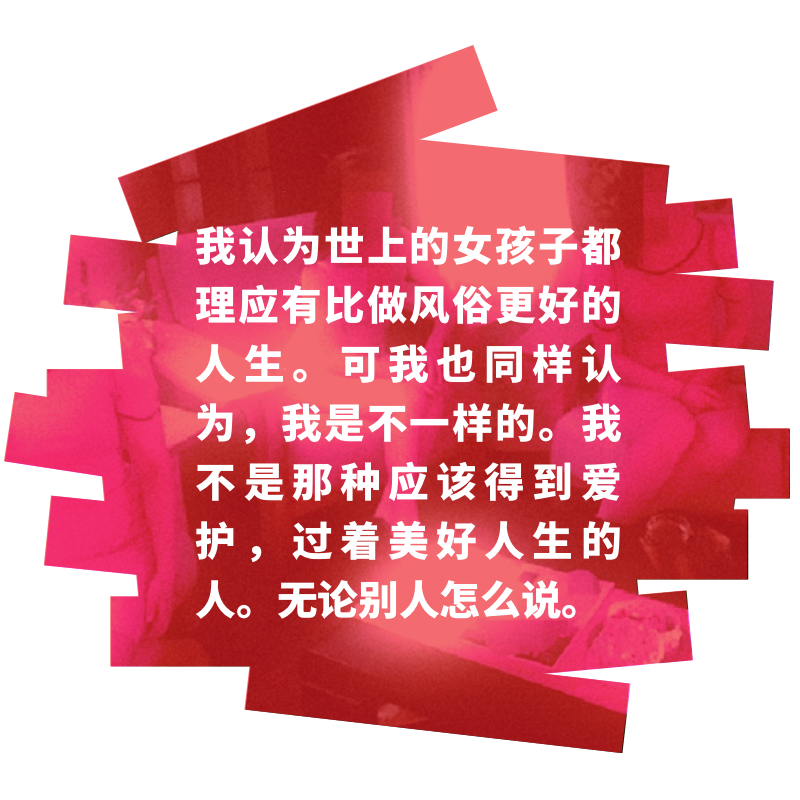
下文中出现的对话内容,均为录音笔记录直接转写文字
2022 年 2 月 6 日,晚上 10 点 09 分,新宿某丁目,X 按摩店
先招待我的,是穿着白衬衫,黑马甲,一身酒保打扮,看起来四十岁左右的一个中国女人。她在前台负责接待,看起来就是这个店内的“妈妈桑”。她看起来非常亲切,肤色黝黑,头发简单地梳着,也没有化妆,就和平时买菜时会遇到的所有中年妇女一样。
她看到我,招呼着,“哎呀,好漂亮。”
“诶,哈哈,谢谢……”
“真好看。一会儿老板过来啊,你先把包放一下,稍等一会儿。要不要喝点啥?”
“没事,不用了。我有点紧张……”
在进店的一瞬间,我就已经给自己编好了一套 “人设” 。我的 “人设”,是一个心思单纯的学生,家境不算好,以前都是乖宝宝,在此次 “误入歧途” 前完全不了解红灯区的事。期望着这样一来,对方也更能对我放松警惕。
妈妈桑热情招呼着我,一边摆着手让我放包,一边亲切地关心着,“哪里人?你不要紧张。”
“那个……”我报了自己真实的出生地。因为我对外地的风土人情都不熟,怕被问出马脚。
“ □ □ 人啊?哎呀,这里很少的。“
我傻傻地陪笑着。妈妈桑又问,“来日本多久了?”
“两年,快三年了。”
“哦,那刚好疫情的时候你来的。”她一脸那真辛苦啊的表情。
“嗯,疫情再往前一年,应该三年了。”
“哦……那还刚好是……”
我们面面相觑地笑了。
“上学?”
“嗯对,上学。”
说着的时候,店里另一个姐姐路过,接着我们的话头寒暄了两句,说起我家乡的事。似乎,流落异乡的人,总会先就着这个话题熟络起来。我们在遥远的东京,说起了海那边的城市。
妈妈桑又问,“多大了?(看起来)很小。”
“二十五。”
“才二十五岁啊……”妈妈桑说。那个加入寒暄地姐姐也看着我,认真点头:“看着就小。”
—— 事实上,在我平时生活的学生圈子里,二十五岁已经比很多人都大了,网上的很多人也喊我姐姐。在歌舞伎町工作的日本女孩,也大多比我年纪更小,从十八岁到二十岁刚出头。二十五岁的,很多都是已经混出名气的陪酒女风俗女了。但在这个店里的姐姐们看来,我完全还是一个小姑娘。她们看起来大多是三十岁,或者三十五岁往上了。有的人的年龄,甚至能做我妈妈。
妈妈桑:“对呀,看着像二十岁似的吼。”
我不好意思地笑着。
妈妈桑还是感叹着,“才二十五岁……真小。”
—— 后来在这工作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,风俗业,尤其是我们这种低端风俗业,年龄小可以说就是一切。我在同龄人里绝不算漂亮的,技术也没有那些姐姐好,更没有其他人“会来事”,但年龄小,在这里就是最大的优势。
好像客人们只要看到我的年龄,就会立刻点我似的。买一个年纪比自己小那么多的女孩子,对他们来说仿佛就已经是一件足够“体面”,足够爽,足够满足虚荣心的事。我好像能理解人是会这样想,却到现在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想。
“你个子好高,有没有一米七?”
“有一米七。” 我点头。
“真好。” 妈妈桑说。另一个姐姐接话,“她进来的时候,(我)就觉得个子很高。”
“其实我今天穿了高跟鞋。不过好像日本人都不喜欢太高的。”
店里的姐姐正色赞同,“对,你以后不用穿高跟鞋。”
“嗯……”
妈妈桑:“很挺啊,看着就好。”
姐姐:“我现在看到二十多岁的就羡慕……“
妈妈桑:“你眼睛都放光了!”
大家笑作一团,我夹在里面,总觉得有些尴尬和不好意思,或者说是有些奇妙的愧疚。
正笑着,店长就进来了。是穿着西装,梳着背头,一口南方沿海地区口音的年轻男人,也就是之前我在微信上联系过的 X 先生。妈妈桑向我介绍,那就是店长,然后用带着奇怪口音的日语对店长说晚上好,另一个姐姐也是一样。
“这么高!”
店长见我第一句话就是这个。
妈妈桑和姐姐热情地打趣着:“对呀,都和你有得一拼了。”“你们比一下,比一下身高。”
又是一番关于身高和我的出生地的闲聊,还有感叹我年纪之小。店长的态度明显沉稳很多,他走到大理石桌的后面,让我在前面坐下,我们中间间隔着那套在店里显得非常格格不入的紫砂茶具。妈妈桑热情地给我摆好了外套和背包,然后和店里的姐姐去后面忙了。
“来很久了吗?”店长问。
“来了三年。”
“三年。在读语言(指语言学校)?还是专门(指职业学校)?”
“在读大学院”
“在读大学院啊。”—— 看起来这在他的店里很少见 ——“以前在国内是读大学的?”
“对,大学毕业了来这里。”
“做什么……哦不是,是学生,学什么的?”
我模糊地回答了,不过和事实没有相去太多。
“那你在中国是在哪儿上大学的?”
“上海。在上海读完大学,然后来日本了。”—— 这是假话。
“来日本挺好,挺好的。”
期间夹杂着客人往来,妈妈桑用日语打招呼的声音。说实在的,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应聘按摩女,要如此详细地问我的学历。可能是为了掌握我的情况?虽然我也觉得,可能是因为中国人总有一种本能,就是非常关心孩子的教育问题。
“多大?”
“二十五。今年刚二十五。”
“你现在那边还有在上吗?”
他说的是我之前在微信里和他提过的,虽然我没做过风俗,但是在日本人开的 Girl's Bar 里工作过的事。
“那边没有再做了。”
“之前那家店在哪?”
“在歌舞伎町……叫 '东' 的。”我大概报了位置和店名,反正这也没什么大不了,然后故意露出尴尬的笑脸,“不过那家店比较便宜,也没什么人去。”
老板对那条路倒是也很熟,哦哦嗯嗯地点着头,并不意外,还问了我是哪栋楼,几层。然后问我,“那他们那边给你多少钱?”
“他们那边是底薪很低的,主要是算一杯酒的 パック (指回扣),这样算。”
“嗯,现在那种不好做了。”
我讪笑着,“确实。”
“现在疫情,人少了。” 老板接茬说道。不过说实在的,疫情对于陪酒店其实并没有什么影响,反而在疫情状况下,日本其他居酒屋不营业,来廉价陪酒店喝酒的客人还略多了些。
当然这些话我就不多说了。我现在扮演的是一个初入红灯区,有些不安,又急需钱的单纯少女 —— 我赶紧抓住话题,低声地,“对……我就是觉得,在都是日本女孩子的店里……而且我光会陪酒,就竞争不过别人……”
“但你日语反正很好。“
“也没有很好……也就是说话没什么障碍。”
“但你读大学院啊,平时要写论文吧?”
“要写的。”
“你什么时候毕业?”
“明年吧。”
“然后呢?接下来做什么呢?”
“后面……还不清楚。我想在日本找工作,但不一定能找到吧。” 我苦笑着。
这句当然也是假话,三个月后我就回国了。不过,如果说了实话,我怕我很难拿到这份工作。夜职界最怕做不久的人,虽然其他行业似乎也是一样。
我总是在说谎,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在这条街上,面对不同人的脸,我总能像呼吸一样自然地说谎,呼吸一样地摆出各种表情。我在歌舞伎町报给所有人的名字都不一样,所有经历和出身都不一样。一开始还可以说,纯粹是为了自我保护,有时候甚至是觉得有趣,但后来就变成一种习惯了。这种时候真的有必要说谎吗?有时候,我也会突然感到困惑。
他顺着我的专业,语气冷淡,却又说了好些文科生以后要在哪就职啊之类的话。意外的,就像一场普通的寒暄,好像我们根本不是在进行风俗店的面试,他只是一个先来日本的前辈而已。聊了一会儿他才问,“你是在哪看到我们店的?”
“是在那个华人论坛……”
“论坛?”
“对,论坛。上面有各种招工的,我点进按摩招工的,然后就……”
一直没有什么表情的老板咧嘴笑起来,“对这个有兴趣?”
“对,就那个,有朋友推荐我去做男士按摩……” 我故意说得比较磕磕巴巴的。
“嗯……”他沉吟着。
我尴尬地笑着继续,“但因为我的签证,就做不了日本那边的店嘛。于是就找了一下,找到了华人那边的。”
“嗯嗯。”对方依然是刚才的表情,“那对你现在来说,收入大概多少可以够?”
来了,最经典最重要的问题。
“呃……可能主要还是看这边的排班。”
“这个看你自己。你要上几天?”
“我现在还在上课……”,我有些迟疑地说。其实这还是假话,我都已经通过答辩,就等毕业式了。可我现在还不清楚这家店的底细,不敢轻易承诺。
“你上课是白天?”
“嗯,一般是上午下午都有课。不过还有不到一个月就寒假了,可能寒假之前我每周做个三四天,寒假之后基本上都 OK 。”
“学校在哪里啊?”
“我学校在那个……”我不好意思地笑着,“早稻田。”
这句当然也是假话。中国留学生的圈子并不大,这是一家背景不明的中国人开的店,我怕他们有什么渠道能找到我。
“早稻田?这么厉害。高田马场的那个?”
“嗯,对。”
“那还挺近的。”
“不过我住得远,高田马场附近的房租还是有点贵。”
“我知道,我知道。你是高学历啊。”
“没有没有。”
“然后你现在来这边的话,晚上就是做到末班车咯?”
“对……”,我说着掐指一算,突然想起一件事,“不对,我下周起就都可以来了。”
似乎是被每周上几天班、每晚上到末班车的话给提醒了。我突然想起,我需要很多钱。我其实没有太多时间用来担心害怕了,于是赶紧换了话术,表示自己可以多加些排班。
“那挺好的。” 对方点点头,“那今天让你来,也就是给你先看一下,我们这里是这个样子的。更了解一下的话,我们这里一个套餐是一个小时,基本套餐是六千 (日元,折合人民币 300 元左右),推油的话是九千(日元,折合人民币 450 元左右)。然后一般来说,客人只来一个小时的比较少,平均都是在两个小时,一万到一万三(日元)。“
我点头如捣蒜。
对面继续,“然后呢,我们这边和员工是对半。没有其他的,就对半。一天的话,可能平均 —— 尤其是新来的话,新人都会比较有人气。像你这样新来的,一天两三万是有的。”
一天两三万日元。
老板说得一脸平淡,我却已经被吓呆了。一天两三万日元,换算成人民币就是一天一千多入账。当然,这大概是骗我的,我心知肚明。赚多少完全取决于多少客人,反正也没有底薪。他大可以说得天花乱坠,这是风俗店招人的基本套路了。
但我还是被吓傻了,我这种人,会有人愿意花一千多买我?买我这么丑的脸,这么丑的身体。你们这些人没事吧?简直想如此大喊 —— 这可是真金白银的钱啊。何况,说到底这只是性感按摩的价钱,甚至没有做/爱。
我第一次去援/交的时候,比现在更年轻,还是标准的女大学生。我还没有和人牵过手,没有谈过恋爱,没有性经验。那时给自己开的价格,也只敢开到三百块人民币。因为我从小就是丑女,黑皮肤小眼睛,头骨的形象像猴子。小学的时候,如果有男生敢和我说话,就会成为所有人嘲笑的对象,女孩子也都不愿搭理我。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丑女。那天,我画着妆,穿着自认为最漂亮的裙子,和客人在地铁站见面,心里雀跃又不安。
然而,约好的人来了,走下车关了车门,只站在那打量了我的脸一眼。我讪讪笑着说得先给钱,三百块……不不,只先给一半定金也行。那个男人看了眼我的脸,什么都没说,掉头就走了。
我现在根本想不起来,那人看我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表情,只记得那辆车在视野里远去,只有我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原地。那是一个暑假的午后,下午三四点,太阳很好,银色车尾巴在金色余晖里闪闪发亮。虽然不记得那人的表情了,但大概是被吓到了吧。一脸厌恶的,觉得我太丑了,被路边突然出现的丑女吓到的表情。
应该是三百块也不值的表情。
我出生在一个经济发展还不错的小城市,那时的三百块钱,在这里,能干什么呢?能吃一顿日料自助餐吧;那天的车站不远处有个游乐园,学校带我们来这春游,我小时候那里的门票是九十八元,现在是一百九十八;大学生难得出一次门放风,两人买两张电影票,再吃个饭喝个奶茶,两人花的加起来也有三百 —— 三百块也没有那么多吧?我可是在和援交比啊?!
但,冷静一想,也对。我自己,和吃一顿自助餐相比,和玩一次游乐园相比,和与人一起看一场精彩的电影相比,我这个人,这具肉壳,好像也真没有能比得过的价值。放在案板上的我,和放在案板上的三文鱼寿司相比,三百块可能是有点太多了。
“嗯……嗯嗯。”我坐在东京的大保健店里,面对着一脸平淡却开口就是你一天能赚两三万的老板,努力不动声色,但还是有些呆滞。算了,也好,反正我的人设也是一个对风俗业不熟的女孩。
老板继续着,“我不知道你以前在那边赚多少,反正……”
“之前一个月赚了八万(日元)。” 我突然很快地接话,接完才觉得不大好,“……没有一个月,小一个月,赚了八万多吧。”
“才八万多?”
“才八万多。” 我梗着喉咙继续,然后不好意思地笑笑,抬高了声音,“因为竞争不过日本女生,哈哈。”
“也太少了。”对面乐呵呵地。
“而且我当时也没有去很多时间。”
“这边的话”,老板悠悠地继续,盯着我的脸说,“你随随便便,可能一周就出五天,那四十万是有的。最低哈。还有每个客人给你的小费,那都是你自己的。加起来十万二十几万,甚至几十万都是有可能的,看你自己。”
(未完待续)
*本文应作者要求匿名发布
//编辑:Rice
//设计:冬甩、板砖兮
//排版:606

